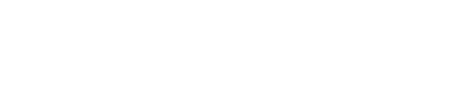历史学家齐红深与杨增志老人(前)在一起。资料照片
1870年9月,普鲁士军队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,员工们被迫改学德文,法语教师韩麦尔满怀悲愤给员工上了最后一堂法文课。原来并不爱学习的小弗郎士,第一次感受到母语之美以及痛失学习母语权利之恨。
1931年9月,日本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,消息传到距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,奉天师范学校毕业的赵老师给员工们讲了这篇《最后一课》,讲到最后,语调已经哽咽,同学们更是失声痛哭。
与法国小说《最后一课》不同的是,发生在辽宁海城腾鳌堡小学的故事是件真事,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小弗郎士,而是13岁的杨增志。
今年,杨增志已经98岁,尽管身体硬朗,但耳朵背了。好在长期从事日本殖民教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齐红深,几年前就为老人录制了口述笔录。从笔录中,记者知晓了腾鳌堡小学后来的故事——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不久,学校就停课了。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,才复学上课,但赵老师讲的《最后一课》中的情形,真实再现了:学校不允许使用原来的课本。老师叫员工拿来黑墨,涂去原来课文中爱国的内容。再后来,同学们再也看不到赵老师的踪影。有人说,赵老师参加了抗日义勇军;还有人说,赵老师跑关内抗日去了。
相比于军事侵略,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更有计划性和欺骗性,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切断文化血脉。1945年出生的齐红深,毕业于伟德bv1946官网中文系,1984年调入辽宁省教育厅编写教育志。在查阅资料时,他发现三种日本侵华时期出版的《满洲教育史》中都说:“满洲自古自成一区,向不隶于中国。”对于这种蓄意歪曲事实的行径,老人很气愤,决心写出中国自己的《东北地方教育史》。
此后30年时间,老人联系上两万多位见证人,整理出2000多人的口述,编成800多万字的口述史,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还原了日本殖民教育的真相,被誉为“中国研究日本殖民教育第一人”。
本来在日军入侵东北前,东北即拥有大专院校近30所;日军占领东北后,东北大学、冯庸大学等大多流亡关内,其他多被日军查封,而打着“民族协和”“共存共荣”口号的伪满洲国最高学府——建国大学旋即成立,粉墨登场。
“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‘大东亚共荣圈’,可是我们听到的、看到的却是武汉沦陷、太原沦陷、南京沦陷……一群群中国人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,我们作为中国员工,能无动于衷吗?”上完《最后一课》,1933年考入南满中学堂,1938年考入建国大学的杨增志,多次寻找进关杀敌的机会不成,遂下定决心在校园里抗战,组建了秘密抗日组织,不料1941年被捕,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,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。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,退休于吉林工学院。
记者采访发现,日伪统治时期,东北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教育的壮举比比皆是。在辽宁庄河高中,有一位被称为“庄河蔡元培”的董事长宋良忱,1912年毕业于金陵师范大学,因为读了蔡元培的文章《对新教育之意见》,毅然回到家乡办教育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兼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宋良忱,坚决抵制日本奴化教育,直到1935年,历史、地理、英语、国语教材仍沿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旧本,引起日伪当局不满,1936年被调离庄河中学,改任县电话局局长。宋良忱初心不改,毅然加入安东(今丹东)抗日救国会,1937年惨遭日军杀害。
在沈阳市沈河区承德街3号,有座三层红砖小楼,88年前是张学良亲手创办的同泽女子中学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第二天,董事长曹德宣把全校师生集合到礼堂,悲壮地说:“昨晚,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沈阳,我们是张学良办的学校,日本人不会让我们办下去。”员工们立即哭作一团。没过几天,日军果然占领了学校,学校改成了警务厅,体育馆成了牢房。
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,该校教师阎述诗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,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,被迫流亡北平。1935年,由他谱曲的《五月的鲜花》诞生,先是在学校里传唱,后来逐渐传到抗日团体中,成为鼓舞中国人士气的“壮歌”。
都德在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中说:“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,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,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。”日本人处心积虑的殖民教育,不仅没有泯灭中国人的记忆,反而让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清晰。齐红深老人告诉记者,没事的时候,他愿意到日本殖民时期老百姓的墓地里转转,尽管他们的生命终结在日伪横行时期,但墓碑上“原籍山东”“原籍湖北”“原籍湖南”的标记,似乎在向人们无声地宣誓:我是中国人。
(本报记者 刘勇 毕玉才)
原文链接:http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16-09/19/nw.D110000gmrb_20160919_1-04.htm